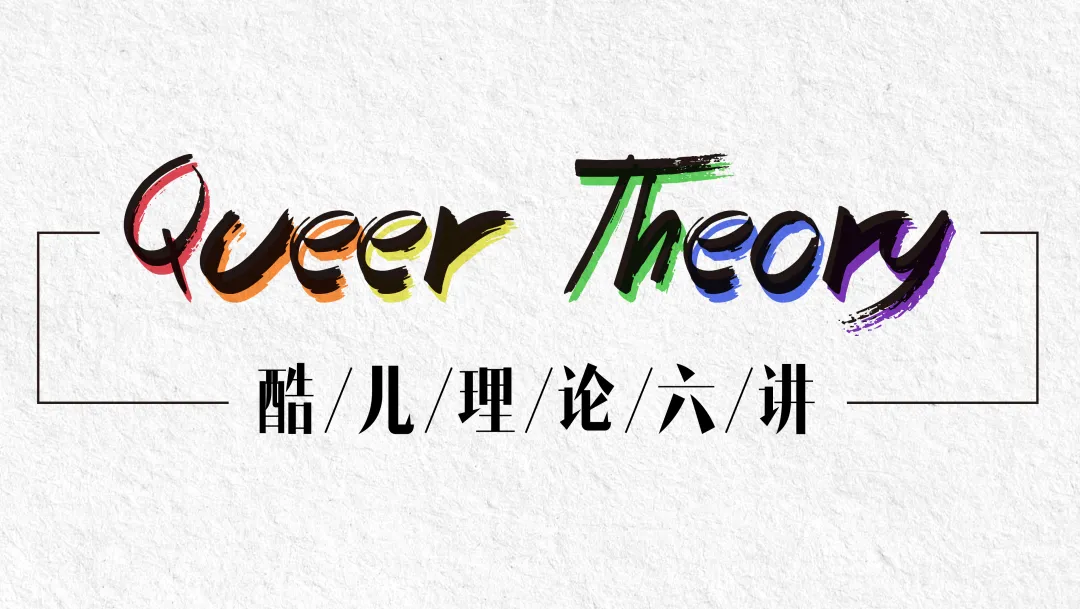异性恋矩阵
我们已经谈到了人类活动根本上的多元性,谈到性别主体的生产有赖于一套规范规定哪些活动是「与性相关的」。虽然现行的规范无疑倾向于将「生理性别二分」和「一男一女」的性行为模式建构为自然状态,但人类活动的现实却给这种规范带来了张力。如果「与性相关」专指某些「两性之间的活动」,那么通过其它形式获得生殖器快感又算什么呢?反过来,如果获得生殖器快感就算是「与性相关」,那么获得这种快感就一定要靠两性之间进行接触吗?比如,即便是自慰,也非要一边自慰一边「幻想着异性」才是自然的吗?
在进行有性生殖的动物之中,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并不算罕见。根据一些性社会学调查,同性之间的情欲即便是在人类之中也说不上多么稀少。这方面的开山之作是阿尔弗雷德·金赛[1]的《人类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Human Male & Sexual Behavior in Human Female)。尽管它收集的数据未必没有偏差、未必全然适用于当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今天看来未必完全经得起推敲),但它首次给出了经验性的、量度性唤起方式的金赛量表(Kinsey scale),根据这一量表将人类性唤起划分为从零至六和X级共八个等级(从只对异性有性唤起,到只对同性有性唤起,以及不对任何人产生性唤起),并在自己调查的范围内给出了每个等级所占的比例。在金赛报告的统计结果中,有37%的男性和13%的女性至少经历过一次与同性达到性高潮的经历[2]。虽然后世的研究大多显示这一数据有些夸张,也给出了更加细致的经验性量表,但金赛报告的确首次严肃地指出了如下基本的社会事实:
[1]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美国生物学家。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主持了大规模的人类性行为研究,为这一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2] 阿尔弗雷德·金赛等编著,《金赛性学报告》,潘绥铭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pp. 189-191, pp. 379-382. [3] 实际上,这项研究非常详细地调查了各超过一万名的男性与女性的性行为方式,并在报告中给予了详细的记录。不止是对同性性行为的调查,对青少年时代性游戏的研究和对自慰的研究也显示出,人类的性实践是极为多元的,传统的「一男一女」「二元性向」模式远远无法概括。后世的许多性学调查报告也都佐证了这一观点。可以参考,例如,B·卡尔(Brett Kahr),《人类性幻想》(Sex and the Psyche),耿文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九章《性取向》。李银河的开创性著作《同性恋亚文化》第二章第四节《同性恋身份的自我认同》也记载了许多不完全是「有意识的同性恋爱」式的同性之间性实践的案例。
所以,这样的规范显然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表述、剪裁了多元的事实。这一规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如何表述、剪裁事实,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表述、剪裁事实」不含贬义,毕竟所有的言说行为都必定涉及到对事实的表述和剪裁。)

盖尔·鲁宾[4]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Traffics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最早对这类问题进行了讨论。巴特勒回忆自己起初就是从这篇论文里读出了「性别麻烦」[5]。
[4] 盖尔·鲁宾(Gayle Rubin),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现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人类学与女性研究副教授。写作广泛地涉及女性主义、同性恋亚文化、SM和性政治等议题。其代表作《性的思考》(Thinking Sex)常常被认为开创了同性恋文艺批评和酷儿理论之先河。 [5]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p. 5.
鲁宾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三个方面的划分出发,将关于性与性别的讨论锚定在了人的再生产这一层面上。她总结道:如果只看到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无偿付出家务劳动而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那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女性受到压迫的全部缘由;然而,马克思自己已经指出,需求本身也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据此,「需要一个妻子」来完成家务劳动(从而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是从把女性放在从属地位的前-资本主义制度继承过来的;进一步地,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6]中所做的,为了讨论与性相关的话题,就有必要更加细致地考察人类繁衍/再生产这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即亲属关系的基本作用[7]。
[6] 恩格斯写作此书的时代,人类学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后世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推翻了此书所采纳的相当一部分实证依据和此书所作的一些具体的历史结论。例如,恩格斯的结论是人类族群普遍经历过一个「乱婚制」的阶段,然而后来的人类学研究几乎没有发现过不存在乱伦禁忌的人类族群。尽管如此,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仍旧是值得采纳的,只是所依据的现实材料必须与时俱进。鲁宾引用恩格斯此书序言作为讨论亲属关系的开始: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7] Rubin G., Traffics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View Press, 1975, pp. 162-165.
鲁宾接下来援引了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8]对亲属关系的分析,试图借此来找到女性受压迫的缘由。亲属关系是人的生产这一层面的生产关系,涉及到人的生产这一层面的支配权。它的所指不必与血缘关系重合(例如,只要养父母愿意,现代社会的制度允许领养的子女享有同亲生子女一样的继承权)。既然人是有性生殖的,为了人的生产这一目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亲属关系便必须包含某种基本的劳动的性别分工。鲁宾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论述进行了如下危险的解读[9]:
[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法国人类学家。其理论直接开启了结构主义这一思潮,对后世的人类学研究、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其因从人类学研究中提取出「交换女人」这一概括而饱受争议,但正如鲁宾的解读所显示的,这一概括实际上蕴含着非常激进的可能。代表作包括《神话学》《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忧郁的热带》等等。 [9] Rubin G., Traffics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View Press, 1975, pp. 162-165.

鲁宾还是隐隐持有某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二分的观念,然而她已经触及到了性别角色划分的社会建构性。她明确地指出[10]:
鲁宾接下来举出了一系列人类学的实证例子,并总结说这些例子都展现出了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基本特征:社会性别分开和强制的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 /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由此,人类性欲组织的基本原则便可被总结为乱伦禁忌、强制的异性恋和两性的不对称划分[11]。此文接下来援引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来解释这一原则再生产的过程,但我们暂时没必要去深究那一面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强制的异性恋。强制的异性恋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亲属关系——所产生的制度性的要求,它就是第一节中提及的那种规范的直接来源。雄性和雌性是生理上不同的,但除此之外的不同还有许多种;雄性和雌性之间的结合当然是有生理原因的,但同性的结合也有生理原因;对性别角色的二分、对非一男一女结合的禁忌,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建构出来的,而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
[10] Rubin G., Traffics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View Press, 1975, pp. 179-180. [11] 同上书,pp. 182-183. 鲁宾在此进行了一点更细致的解释,即不同的族群因为其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可能会对「两性划分」有不同的规定。她举例说,莫哈伏人(the Mohave,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制度允许一个生理构造上的男人通过某种仪式而被认定为女人,女人也可类似地被认定为男人,而后可以同生理性别相同的人结婚。这在他们的标准下是「异性恋」的。但莫哈伏人不能理解「双性人」。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更加危险的暗示:援引一下那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古老辩证法,这是不是暗示着,如果辅助生殖技术进一步发展开来,强制的异性恋将很可能彻底丧失其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呢?这是不是暗示着,生产力的提升将会容许一种无性别的社会形态出现呢?
不过还是先把目光拉回过去和现在,看看这种基本的「强制的异性恋」的规范导致了什么后果吧。首先,它当然导致了一种将男女建构为不平等的性别的社会格局。显然,劳动的性别分工似乎并不必然「从逻辑上」导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然而人类社会的其它历史条件却几乎都导致了这种后果,而这种格局也为资产阶级时代所继承了。在资产阶级时代,体力上的差别已经不再是个体进入社会化生产的限制,然而前时代的遗产并不会被社会轻易地抛弃。如鲁宾所举的例子,资产阶级时代也需要将家务劳动推脱给小家庭自己来完成,而前时代遗留下来的性别分工格局正好可以被借来使用。这正像马克思所评论的:一切死去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强制的异性恋」这个术语后来被阿德里安·里奇[12]在文章《强制的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中专门进行了论述;同一时代的莫妮卡·威蒂格[13]也在其惊世骇俗的演讲《直人思维》(The Straight Mind)提出了类似的说法:「直人思维」或者「异性恋的契约」。里奇和威蒂格都集中火力猛烈抨击了强制的异性恋所造成的文化后果。威蒂格的概括是,「直人思维」将所有「非异性恋」的对象都视为一种统一的他者,它起到的效果是告诉人们「你要么是直人,要么什么也不是。」[14]里奇的论述要具体一些。她重点强调的是这种「强制的异性恋」通过否认女性的性而将女性限制为男性的附属之物,呼吁一种直接的针对强制的异性恋的反话语:女同性恋式的交往。
[12]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美国诗人、散文家和女权活动家。 [13] 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法国作家、激进女性主义与女同性恋活动家。 [14] 可参考Purple于2017年9月发出的推送《他山之石 | 直人思维(重译)》。
如果再结合强制的异性恋的「禁忌」本质,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里奇和威蒂格论述的是什么——比鲁宾更进一步,她们指出的是,强制的异性恋规定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之外的性都是违背基本的社会原则的、反常的(extraordinary)、从而是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如果要反思强制的异性恋如何把「非异性恋」建构为不可理解的,那不妨将其与习俗进行类比——当然,强制的异性恋本身就可说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基本习俗。鲁宾就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类比[15]:如果我们有谁能平静地假设我们也会按照习俗和舅舅的女儿或者姑姑的儿子结婚,那可太反常了。
概括起来,还是引用巴特勒的论述[16]:
……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的」(intelligible)性别是那些建立和维系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与欲望之间的一致与连续关系的性别。换句话说,那些不连续、不一致的幽灵也只能在已经存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规范下才能被设想。幽灵一直是被律法所禁止、所生产的——那些律法企图在生物学性别,文化建构的性别,以及两者通过性实践在性欲展现方面的「表达」或「效果」之间,建立起因果的或者外显的线索。 认为可能有某种关于性/别的「真理」——福柯的反讽用语——这种观念正是通过管控性的实践而生产的。这些管控性的实践通过一致性的性别规范矩阵生产一致的身份。对性欲的异性恋化要求、创建了「阴柔」与「阳刚」这两个明确区分且不对称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其中两者又被理解为「女性」与「男性」的外观属性。我们通过文化矩阵来理解性别身份,而这个文化矩阵要求某些「身份」不能「存在」——这是指那些社会性别风貌不符合生理性别特征的身份,以及欲望的实践并非「根据」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而来的那些身份。
[15] Rubin G., Traffics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View Press, 1975, p. 183. 这样的习俗当然在某些人类族群中存在——不同的族群对乱伦禁忌有不同的规定,按照有些族群的习俗,与舅舅的女儿/姑姑的儿子结婚才是唯一准许的结合,而除却这种「舅舅的女儿恋」「姑姑的儿子恋」(鲁宾的原文如此)之外的结合不论是「异性恋的」还是「同性恋的」都是禁忌。 [16]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pp. 23-24.

这就是那种规范起作用的方式:设定好二分的性别、性倾向和性别规范之后,将所有的事实都剪裁到与这种设定相一致的程度,而那些超出规范的或者被镇压,或者只能够以这种规范所规定的方式去谈论——这当然就导致了「不可理解」。也就是说,「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区分也是基于这套规范的。我们终于达到了一个比「强制的异性恋」涵盖更多社会性的概念: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巴特勒写道[17]:
[17]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p. 6的脚注。宋素凤将matrix一词翻译为数学术语「矩阵」,因为这抓住了「网」这个能指所引发的联想。Matrix一词还有模板、母体等等多重意思,但在这里,暂且还是沿用宋素凤的翻译。
对于巴特勒所谈论的东西,只要留心观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我们的规范规定了男性应当阳刚、女性应当阴柔,于是「娘炮」和「男人婆」便成为了可以被肆意取笑的、需要管控的。我们的规范是强制的异性恋式的,只有「异性恋式」的性行为与亲密关系——区分插入方和接收方的角色,并认为插入方是阳刚的,接收方是阴柔的——才可以被理解,于是同性情侣首先常常不能被接受,即便是接受了也常常会被人问这样的问题:你们做爱的时候,谁当「男人」,谁当「女人」?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谁当「丈夫」(勇于打拼/粗鲁直率的「男人」),谁当「妻子」(温柔贤惠/娇嗔可爱的「女人」)?——在同性情侣之间,也只有存在这种稳固的分工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规范把某些特定的性别劳动分工视为理所应当,从而为无偿占有女性的家务劳动提供了依据。我们的规范是强制的异性恋式的,它要求人们必须缔结某种特定的亲属关系——异性恋专偶制家庭关系,繁衍子嗣并承担起养育的义务,于是不结婚的人(特别是女人)、不生育的人(特别是女人)便成为了可以被取笑、应该被指责、在制度上应该被压迫的……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异性恋矩阵不是自类人猿诞生以来就有的,也不是平滑无缺的。相反,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调整着,因为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博弈每时每刻都与它产生张力。反对霸凌的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为「娘炮」和「男人婆」、为性少数群体撑开了生存空间。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可能,在此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每时每刻都在迫使劳动的性别分工进行重新定义。道理很简单:对上位权力的反制也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或者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反过来,异性恋矩阵尽管不断地自我调整着,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变动。它仍旧每时每刻都 在施加着暴力。为了看清楚这种暴力的形态,看清楚其下权力关系的博弈,我们就需要对暴力的运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 TO BE CONTINUED /